湮灭之城
7月13号那天,是他21年的忌日,全球古典乐坛上的风云人物与无数音乐爱好者都深深怀念他!我的“发小”兼超级古典音乐迷,是他的忠实粉丝。
他并非完人,却一生追求极致;他有着孩童般的纯真,却对音乐感悟极深,见解成熟而独特;他对所有的曲目都了如指掌,却懂得选择以及该如何选择;他注定是众人仰慕的大师级公众人物,但却憎恶聚光灯,不屑与达官贵人为伍;他所录制的CD寥寥无几,但却是张张精彩,早已成为收藏者的最爱;他在舞台上收放自如充满自信,但却在内心深处常常沮丧、自卑、孤独;他痛恨一切商业运作与包装,却对因过于商业化而广为众人诟病的卡拉扬“情有独钟”,每每路过,都要去他的墓前谒拜;他是名副其实的帅哥,从大学开始就很有女人缘,且常常爱慕之心泛滥,但却对自己的结发妻子深深依赖,以至于妻子去世仅半年他便追随而去;他以乐坛“坏脾气”著称,屡屡在排练中因一言不合便佛袖而去,将一众目瞪口呆的乐手晾在原地,可是凡与他合作过的乐团与乐手回忆起他来,都充满怀念、记得与他在音乐上的鱼水交融……
看他的指挥完全是一种美的享受,音乐在他优雅的手势中自然流淌,那沉浸在音乐中的肢体的舞动,分明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舞者,伴随着动人的音乐,在众目睽睽的舞池中央翩翩起舞,自信洒脱,迷倒了现场的男男女女。

就是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年轻时却栽在一位姑娘身上。那姑娘是一位漂亮的斯洛文尼亚芭蕾舞演员,他在指挥时认识了她。
于是他主动上前套近乎:“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谁知那姑娘竟一点面子都不给:“抱歉,没兴趣!”
当然这对于契而不舍的他来说不算什么,无情拒绝本身反倒让他欲罢不能,更激起他的“斗志”,接着便是各式各样的冒险行动,最终他成功了,他们结婚了。从此,这位小他7岁的妻子斯坦尼斯拉娃(Stanislava Brezovar)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稳定来源。
但那只是他的一面。
据她姐姐回忆:他从小就瘦弱不堪,以至于母亲一度担心他是否能活下来。小时候他学过一首小歌:“海鸥,飞到赫尔戈兰岛去,代我亲吻我爱的女孩。我孤独,我被人遗弃,我渴望和她在一起。”他唱这首歌时如此伤感,令人动容。
也许孤独和忧郁早在童年便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就是被广泛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1930-2004),一位出生于德国的奥地利指挥家。
2004年7月19日,全球各地的通讯社才从斯洛文尼亚获悉,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卡洛斯·克莱伯已经去世。法国《费加罗报》更使用了充满惊愕与愧意的新闻标题:《哦,对不起,我们昨天才知道他去世!》
这迟来的报道,代表着一个让所有熟悉并关爱他的人不愿面对的事实:这位指挥家在三天前就已悄然下葬了,葬于7个月前先他而去的妻子墓旁,它坐落在斯洛文尼亚利蒂亚(Litija)附近的一个小村镇,那是她的故乡。或许是因为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缘故,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皈依了基督。
他是一个可以追随、却不愿让人靠近的人。
他第一次消失在公众视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宣布退休隐退,短短一句“我要去蓝色世界了”震惊了古典乐坛。他为世界付出了太多,但人们对他的期望却远不止于此。人们总是想象,如果卡洛斯能演绎威尔第的《安魂曲》会是怎样?如果他能继续指挥10年会怎样?
但人生没有“如果”。
没有人会想到,选择隐居的他,会与一位斯坦福音乐系学习指挥的大学生有着一段不解之缘。1987年暑假,年轻的巴伯(Charles Barber)与同学踏车旅行。行间他们被电视节目里交响音乐会指挥的动作所吸引,之后才知道那就是卡洛斯·克莱伯。此后,巴伯开始收集、阅读和观看有关他的一切资料。他迷上了卡洛斯,他寄信给卡洛斯,希望能够成为他的助手,跟他学指挥,但卡洛斯没有接受巴伯的请求,不过从此他们开始通信。2011年底,也就是卡洛斯去世7年后,已经是温哥华城市歌剧院艺术总监的巴伯,将他和卡洛斯的通信积集成书,即《与卡洛斯的通信》(Corresponding with Carlos——A Biography of Carlos Kleiber)。书中让世人看到了那个神情腼腆而且似乎不太自信的指挥大师敏感、幽默又轻松的另一面。
他即使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也从未摆脱父亲的阴影。在给巴伯的信中,卡洛斯提到:“埃里希(他父亲,Erich Kleiber)是他生命中一位不朽的人物,他控制欲强,令人无法抗拒,并且是他整个音乐感知方式的核心……”
年轻时,他的父亲曾力阻他成为指挥家,当时他小心翼翼地向父亲提出自己想当指挥家的梦想,却被父亲蛮横拒绝:“有一个克莱伯就够了!”
卡洛斯毕竟是卡洛斯,他并没有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当他于1954年开始指挥生涯的时候,他甚至以艺名Karl Keller示人,为的是避开父亲的光环。在波茨坦的第一场排练,年轻的克莱伯完全没有初登舞台时的拘谨和客套,他与乐队一起排练了十余次,将其精益求精的态度充分呈现出来,多年来形成了他独具一织的排练风格:他经常打断乐手的演奏,清晰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故而有“绝不容忍错误的指挥家”的称谓。在他几十年非常有限的演出中,他对每一场演出首先考虑艺术上是否达到自己的标准,是否合乎他的期望,任何一场演出他都要力争做到尽善尽美,否则宁肯取消也决不凑合。他那种一丝不苟、宁缺勿滥的境界,是别的更注重效益的指挥家难以达到的。
然而,他始终对自己的父亲推崇备至。对这位曾与富特文格勒、托斯卡尼尼、瓦尔特、克伦佩勒齐名的指挥家父亲,他自愧不如,视其表演为完美的巅峰,他在写给挚友的信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崇拜:“这是《玫瑰骑士》的杰作,无与伦比,未经雕琢,精彩绝伦,独一无二,气势恢宏,从头至尾都堪称真正的维也纳之作!还有那圆舞曲!无与伦比!……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作品了!”
但其实,在众多乐迷看来,卡洛斯不仅在天赋、才华、情感、直觉、敏锐度、精细度以及指挥风格上都超越了他的父亲,而且在对音乐的深入剖析与理解、与各个乐手的有效交流以及对整个乐队的掌控等方面更是无人能及。

有人评价:他的表演,是将细致精准与充满激情的即兴演奏完美融合的典型。他注定是一位具有传奇般故事的完美主义者。
与当代指挥巨匠卡拉扬霸道、粗犷的风格截然不同,克莱伯的演奏风格低调、柔和、细腻,与人们对每部作品作曲家试图传达的意境完美契合。随着他登上舞台,音乐、乐谱和作曲家即刻融为一体,听众瞬间便被弹射到大气层之外,在那里,只有天体的谜团在耀眼的阳光中翩翩起舞,在他魔术般的指挥棒下,灵魂也绽放出笑容。
受人尊敬的指挥家贾维(Paavo Järvi)讲述了一则关于他的轶事,那是他指挥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的一个有趣场景:卡洛斯一出现就赢得了观众的起立鼓掌,那掌声比歌剧结束后大多数演出的掌声都要持久……就在剧院渐渐暗下来、歌剧开始进行时,有人从过道走过来大声说:“哇,伙计!”大家都回头看,发现竟然是伯恩斯坦!当时维奥莱塔演唱的音调非常高,之后高音部分渐弱,一种令人惊叹的渐弱,你甚至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真的,那是我记忆中最安静的时刻。然后就是我身后伯恩斯坦的那个夸赞的声音,音量非常大。
他是地道的剧院指挥,相较于剧院近600场的演出场次,他终其一生在音乐厅指挥过的演出场次极为有限,总计不过96场,而跨度则长达30年。这数量甚至远少于同时代许多指挥家每年上百场的频率。像卡拉扬,一生指挥过多达3500场的演出。而伯恩斯坦,也超过了1500场。即使如穆蒂、巴伦博伊姆等现代著名指挥家,在指挥生涯仍在继续的过程中,也都已轻松突破了1000场。
2010年11月,英国《BBC音乐杂志》(BBC Music Magazine)曾面向当今100位世界顶级指挥家发起过一项投票,旨在评选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位指挥家”。该评选不设候选人,每人可自由推荐3名,包括可以投票给自己。俗话说“文人相轻”,这种由指挥家自己从专业的眼光评出谁是“最佳”的方式,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2011年3月公布的最终结果令全世界惊讶:卡洛斯·克莱伯居然名列榜首!其后依次为伯恩斯坦、阿巴多、卡拉扬、哈农库特、西蒙·拉特尔、富特文格勒、托斯卡尼尼、布列兹、朱利尼……
人们不禁会问:他为什么会排在第一位?
也许是因为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以及知道如何通过乐队将其完整地呈现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在排练和演出中与众多乐手的真诚交流和鱼水交融?也许是因为他的指挥风格独树一帜,把握精准、细节清晰、潇洒自如,极具感染力?也许完全是源于他低调的为人、充满矛盾的个性以及为世人留下的众多的迷?……
BBC音乐杂志副主编杰里米·庞德说:“邀请100位当今伟大的指挥家说出他们的偶像和灵感来源,这真是一次令人着迷的经历。尤其是当这么多人提到卡洛斯·克莱伯时,他一生指挥的音乐会场次比大多数人指挥的场次加起来还要少。克莱伯对细节的极致关注、对音乐的纯粹热情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奏水平毋庸置疑——或许‘少即是多’才是通往真正伟大的真正途径?”
当代乐团音乐总监苏珊娜·马尔基(Susanna Mälkki)评论他:“卡洛斯·克莱伯为音乐注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没错,他的排练时间确实比当今指挥家多五倍,但他当之无愧,因为他拥有非凡的视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对细节的关注也真正鼓舞人心。”
克莱伯的传记作者、好友兼笔友查尔斯·巴伯认为:成就他传奇而非凡的职业生涯的,是他独具一格地将德国分析、形式和纪律的严谨性与拉丁舞的活力、律动和喜悦融为一体。
英国《留声机》杂志如此评价他:是什么将卡洛斯·克莱伯推向了近乎神秘的高度?是超越自我界限的难忘体验,也是他在最后一次排练的最后几分钟愤然离场时的无助感。这并非矫揉造作,而是深切绝望的表达,即便乐团已展现出最高水准——或许正因如此。他的性格充满极端矛盾:他时刻担忧灾难,却又乐于与音乐家们私下交流。他拥有丰富的曲目,却又只演奏寥寥数部作品。他的怒火可能发泄在任何人身上,但他与孩子们的互动却流露出珍贵而脆弱的温柔。艺术没有上限。然而,每一代人都需要至少一位艺术家来诠释这一点。克莱伯为我们触及星空;即使他最终崩溃,他依然证明了星空的存在。
他是一个深刻且与世隔绝的艺术家,远离了公众的视线,过着极为私密且脱离喧嚣的生活。尽管他已经是20世纪最受尊敬和崇拜的指挥家之一,但他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异常低调,从不接受媒体采访(记录中的仅有的一次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他拒绝了所有顶级乐团常任指挥的邀请,即使是面对1989年卡拉扬去世后柏林爱乐的盛邀也是如此。当时乐团的乐手已得知他无意接手,但之后的数次投票,众望所归的依旧是他。
他的古典乐坛上的巨大声望与他的采取的低调态度和自我隔离,更加强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有关他的故事在业界广为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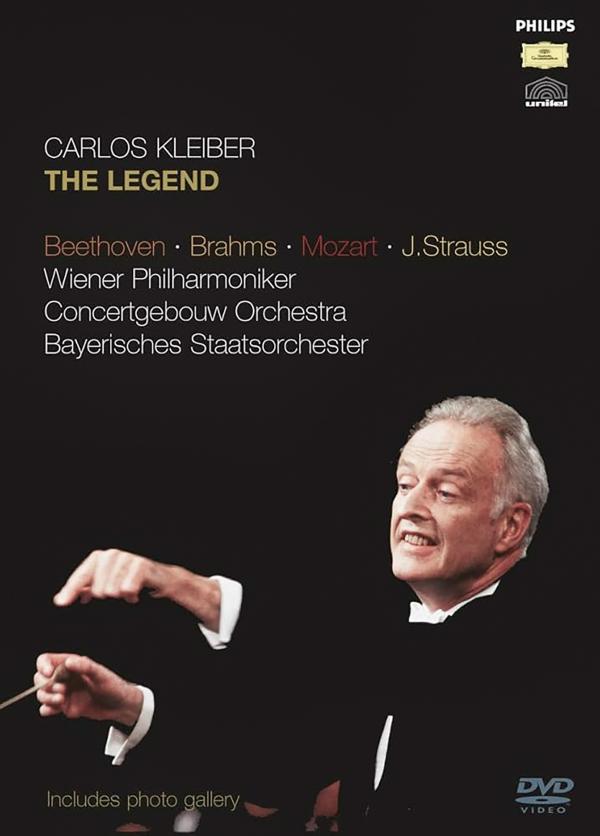
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家迪特尔回忆起与卡洛斯的排练,当时排练的是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卡洛斯那种发自内心的“激发音乐家灵魂”的能力让这位长笛手铭记在心,他唤起了舒伯特濒临死亡时深深的忧郁。音乐以低音提琴开始,然后是一段停顿,音乐停止了,然后是“五度”……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唤起了整个乐团的恐惧。所有音乐家都多次演奏过这首交响曲,但和他一起演奏,仿佛像是第一次。
还有一次,卡洛斯想要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他找到卡拉扬,请他给自己讲解。但卡拉扬事后告诉我们,他与卡洛斯待了4个小时,但他从来没有在4个小时里像和卡洛斯一起时学到的这么多,因为卡洛斯把整部乐谱都给他讲解了一遍。
在与卡洛斯合作的乐队里,每个乐手都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有机体、一件乐器。而他,就如同用这个有机体即兴演奏。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他的手势非常清晰,他从不刻意练习技巧,却总是致力于音乐的意义、心理学及情感状态,最终却同时获得了完美的技巧。他就像是与灵魂而非工具合作,他让灵魂绽放笑容,传达出一种无限的喜悦,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至福。如果音乐能够摆脱泥土束缚,开始飞翔,那么他做到了,他是一位真正非凡的人。
是的,正是他的即兴发挥和出人意料的音乐性,让每场音乐会都成为一次全新的体验。
曾担任斯卡拉歌剧院首席小提琴长达30年的朱利奥回忆,我有幸在斯卡拉歌剧院工作,因为最伟大的指挥家都曾在那里指挥,我认识并合作过的乐团指挥不计其数,我与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共处一个音乐社群。但我必须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卡洛斯;他的排练,以及他组织音乐演出的方式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难以置信!在排练《奥赛罗》时,他从来不会连续排练超过两三个小节,并且他会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告诉每个人要做什么,这完全是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乐团的管理人员有些着急了,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从头到尾排练过。他不知疲倦地做某件事,最后终于爆发,演出中每个乐手都跳了出来,他的指挥棒发出了嘶嘶声!那是带着爆发力的效果。
他非常人性化,更是一个可以超越音乐本身、拥有对音乐进行内省的人,他展现了感性和文化(不仅仅是音乐)的和谐统一,他通过音乐引领人们走向幸福的维度。人们不得不感激他,因为他让他们与他一同进入这个世界!他所强调的技巧,那种细腻,分明就是爱抚,他说:“用爱抚的弧度来演奏,但不要,不要在手臂上,是在手臂的皮肤上。”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大概是1988年,我们一同来到日本。这次他只要求排练整部《波西米亚人》三个小时就够了,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斯卡拉大剧院确保首演时乐团的原班人马。乐团为难地告诉他,乐团里已有4个人退休离开了。卡洛斯不干了,当即答复:“好吧,不演了,我不去了。”
无奈的乐团管理层找到我说:“听着,弗兰泽蒂,你一直和他保持良好的联系,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好请你去向他解释吧,我们不可能让退休的人回来。”
我记得我去对他说:嗨,大师,他们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已经被更有价值的人取代了。”
看着我问:“你能保证吗?”
我说:“大师,听着,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很棒的人,而且只离开了这4个人,其他人都在,不会影响排练和演出的。”
他说:“很好,谢谢你!”他接受了我的劝告。
卡洛斯就是这样,通过与乐队合作赋予了乐曲独特的情感,在许多人看来,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成功地赋予情感,他有能力将人们带入另一个世界,那是他的世界,不,那不止是他的世界,他赋予了人们超越他人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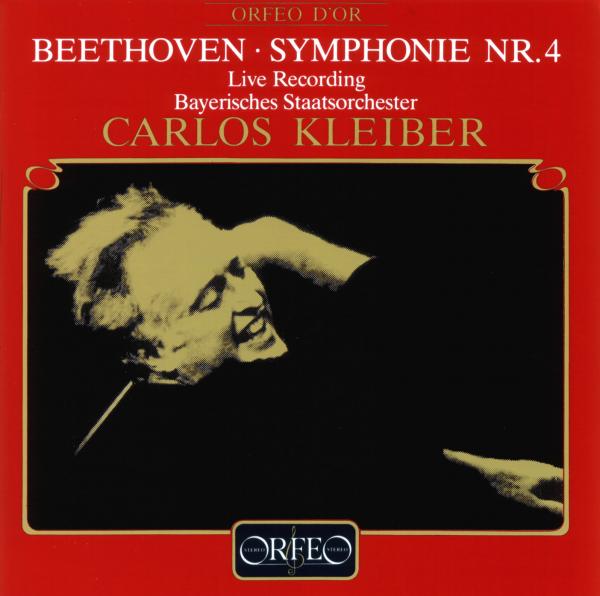
同为指挥大师的阿巴多如此评价卡洛斯:他能完美地说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而且发音十分纯正,这使得他与不同的乐队和乐手交流起来游刃有余。在这背后,是创作音乐的热情、快乐和对音乐的热爱。他是一个伟大的完美主义者,他总是以最丰富的想象力去探索……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想象力,他对音乐本身充满了敬畏。他的笑容恰到好处,很少有人能拥有这样的笑容,当人们在音乐中创造出美妙的东西时就会微笑。卡洛斯内心是安宁的,但那种对音乐的激情和热爱在某种程度上迷住了所有人,无论是乐团、观众、歌手……他向人们传递出的、创作音乐的巨大喜悦让每个人都为之疯狂。在我听过他的所有作品中,无论是贝多芬、勃拉姆斯、威尔第、施特劳斯或是瓦格纳,都是杰作。但或许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玫瑰骑士》,之前我已经习惯去维也纳听卡拉扬指挥的《玫瑰骑士》,卡拉扬指挥的《玫瑰骑士》非常精彩。但与之相比,卡洛斯指挥的《玫瑰骑士》毫无疑问更加出色。
还有富有盛名的俄裔美国钢琴家霍洛维茨(Horowitz),当他从电视转播中偶然见到克莱伯后,惊喜不已,遂与他联系,商谈联手演出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事宜。岂料合作在即,霍洛维茨突然离世。
著名钢琴家里赫特在上世纪70年代观看了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卡洛斯指挥的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演出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有幸遇到的最伟大的指挥家。我相信只要我还活着,就再也听不到像这样的演绎了:这才是真正的《特里斯坦》,卡洛斯将音乐推向了沸点,并一直保持了整晚。从演出结束时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你会感受到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指挥。”
另一位杰出且内敛的音乐家是波里尼,他与卡洛斯虽然从未合作过任何作品,但却是他的挚友。他这样评价卡洛斯: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音乐界正在丢失的音乐遗产的钥匙已交付到他的手中,那就是道德、对作曲家细节的忠实、一丝不苟、完美主义和自我批评。相信人们不禁熟悉他,而且不会忘记他的遗产。他回忆起当年与乐队排练《魔弹射手》序曲的一次邂逅。当时卡洛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丝毫不错过排练的瞬间,他提出的建议或要求远超音乐技巧,更注重乐句,更注重全面的音乐观察,并且运用了音乐之外的影像,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鲜感,毫无保留地向整个乐团表达他的想法。乐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因为很明显,他们正在经历一场与其他任何指挥家都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们甚至把他看作是来自月球的人,因为他们通常习惯于技术建议,却从未领受到有关高水平演奏要求的建议。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他与这支乐队逐渐建立了某种默契。要知道,指挥和乐团的出发点常常是南辕北辙,彼此都视对方为珍稀物种,想要达到默契谈何容易,但卡洛斯在不知不觉中做到了。
曾在斯卡拉大剧院和大都会歌剧院饰演女主角的女高音米雷拉·弗雷尼对与卡洛斯的合作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大都会歌剧院与帕瓦罗蒂一起排演《波西米亚人》,帕瓦罗蒂扮演鲁道夫,我扮演咪咪。那是卡洛斯在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次登台,我们到达排练场时,我发现他有点紧张,每当遇到一些他不熟悉的新事物时,他都会稍微隐藏一下自己。但排练第二幕后,他走到我身边说:“米雷丽娜,我得问你一件事。听着,我想我不会和乐团一起排练。”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要知道,之前他从来没有与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团合作过,现在他竟然想要越过乐队排练,直接带妆彩排?于是我说:“大师,不,听着,卡洛斯,我们演过那么多波西米亚人,我很清楚你想要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也许问题出在你身上!”
可结果,他真的越过了乐队排练!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首演之夜非常成功,整个乐团为他疯狂。接下来,我们合作了一辈子……
跟他合作真的很棒,一起创作音乐真是太棒了!一天晚上,在《波西米亚人》最后一幕开始前,他来到我的化妆间,说:“你知道吗,米雷拉,我们需要做些调整。”我不高兴了,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昨天告诉我呢,这样我至少有机会在家试试?你最后一幕开始前才来告诉我这个?”他说:“听着,如果你愿意,我们试试;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就不做调整。”我只好妥协。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建议的处理方式更好。卡洛斯非常朴素。在外面,即使在纽约街头,他常常穿着牛仔裤,脚蹬便鞋,手里提着个塑料购物袋,超市里进进出出,他看起来十分普通。可是当他登上领奖台时,他却焕然一新,他点燃了自己,用他内心深处的一丝光芒照亮了别人,那种创作音乐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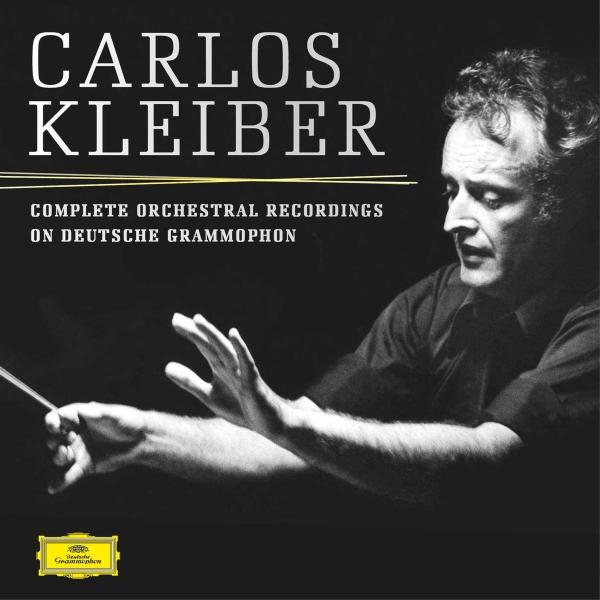
曾是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巴松波廷格尔,勾勒出这样一幅卡洛斯的轮廓:在技艺与天马行空的幻想之间不断摇摆。他是一个能打开许多扇门的人,经常用图像、例子、气味、幻象和梦境来表达。他讲故事,对他来说音乐就是故事,他只想让音乐家们远离底层,和他一起排练的每一次都很特别。他的激情、喜悦、疯狂,他的攻击性,他对音乐的深刻信仰,使得他的语言极具感染力。要知道,音乐中有些东西难以描述:有些人拥有,有些人没有。但他有,他痴迷于音乐,并成功地传达了它。他有着深厚的、对音乐的爱,并成功地将其传达出去,这是一种非凡的品质。此外,他的肢体语言格外精致,就像签名一样,绝非抄袭。那是一种无需言语就能诉说的肢体语言,眼神、面部表情,还有手臂,尤其是手臂。他知道如何积蓄能量,然后释放它,张弛相间、乐句强弱的平衡。
卡洛斯的姐姐在回忆起弟弟时自我调侃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但我弟弟说我懂音乐。他说:“懂音乐和做音乐家其实没什么区别”。多年来,每当人们问我们姐弟俩:“你父亲是音乐家,那你们呢?”我们俩总是回答:“我们不是音乐家,我们只是受过教育的大众。”可是后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改口:“哦,我弟弟是的!”
因为卡洛斯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所以不少人希望通过迂回找到了他的姐姐。但姐姐并不配合,她回忆:他非常难以接近,所以人们不得不杜撰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几乎没有人见过面具背后的那个人。这些媒体人自己联系不上他,就试图说服我充当中间人。但我说:“我拒绝和别人谈论他做的事情。如果他自己都不接受采访,我又能代替他做什么呢?你还指望我做什么呢?”
卡洛斯面对公众的两次隐退都令人扼腕。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乐坛从此再难见到他的踪影。而第二次他更是悄无声息地永久地离开了,全不顾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朋友和仰慕者的思念,甚至就连写一张卡、送一束花、写几个字去表达一下哀思的机会都不给。这似乎印证了他所喜爱的庄子的话:
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渔父》)。
有关他的回忆记录影片干脆就以《了无痕迹》(Traces to nowhere)命名,取其意:人的一生似乎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痕迹。
尽管如此,他终究留给人们、并且挥之不去的是:那张英俊的脸、修长的身材,以及指挥台上风度翩翩、激情四射、魅力无边的画面。
还有,很多,很多……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

